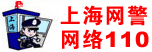不久前,国际译联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2014“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授予许渊冲。他由此成为该奖项自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亚洲翻译家,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在国际翻译界获得最高奖的第一人。
1999年,许渊冲还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许渊冲
江西南昌人,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20世纪40年代,先后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和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1983年后进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任教,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专家。
作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迄今为止许渊冲已出版各类译著超过150本,涵盖汉英、英汉、汉法、法汉四种类型,被业内专家誉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
他上世纪50年代翻英法,80年代译唐宋,将中国古典文学如《诗经》《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翻译成英法文,在法国出版时引起热议,这些作品被誉为“最伟大的中国诗词”。
他将中国古典四大戏剧《牡丹亭》《桃花扇》《西厢记》《长生殿》翻译成英文,国外友人称其可以和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媲美。
许渊冲在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4平方米工作室
1921年百花欲开、新月渐圆之时,江西南昌的一户普通人家里,一个口张得特别大、哭声特别响的男孩出生了。家里人给他起名许渊冲。
如今,他已年过九旬,依旧声如洪钟。他一边拍着自己的身体,一边中气十足地说:“眼睛、耳朵、牙都不行了,走路腿有点累,手有些软,但我就只有一点:声音大!”
许渊冲坐在10平方米不到的会客厅的书桌旁接待来访。会客厅里,年代久远的沙发背后,是一整面墙的书。四层、上百本的书用简单的隔板隔开。要知道,这些书大部分是许渊冲一生的作品和译著,他的作品在中英美法四国已出版150余种。
93岁的他没有到达柏林的颁奖现场,仍在北大畅春园的不到4平方米的工作室里,为他的下一个目标奋斗—“我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争取两个多月翻译一本,计划五年内完成莎翁全集。”
他曾形容西南联大的老师闻一多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形容朱自清是“闲云潭影日悠悠”,也称自己“诗译英文唯一人”、“不是院士胜院士”。
生于军阀混战时期,许渊冲受到最大的教育就是好好读书。他还记得爸爸说过:“我这辈子算是完了,只有叫下一代好好读书,才能为家庭争口气。”
他儿时最崇拜的是三姑爹“式一叔”。当式一叔写的剧本《王宝钏》在闪耀着霓虹灯的伦敦和纽约上演之时,小渊冲就记住了两点:英国的萧伯纳都喜欢式一叔的作品;爸爸说式一叔回国时给丈人带的银元一辈子用不完。
小学四年级开始,许渊冲开始学习英文。当时没有国际音标,许渊冲被没有中文读法的字母WXYZ的读音难住了,二堂兄编了口诀 “打泼了油,吓得要死,歪嘴”。许渊冲这才记住。
因为读音规则别扭,许渊冲认为英文没有道理就失去了兴趣。高一时,他不喜欢英语的语法结构。那时的他更爱国文课,文字学和文学史都得了第一名。
高二是许渊冲英语进步最快的时期。记忆力极好的他轻易背下了教材《英文短篇背诵选》里的30篇英文课文。从那以后,他的英文写作思路一下子打开了,成绩从中等跃居到班级第二。
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
1938年,许渊冲考入了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外文系。同级校友还有如今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经济学家王传纶、两院院士王希季。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是许渊冲疯狂吸收知识的时光。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课“空前绝后”般精彩。每周许渊冲在昆华农校的大教室里听来自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三小时的课—闻一多讲《诗经》,陈文典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冯友兰讲哲学,柳无忌讲西洋文学,萧乾谈“创作与译诗”,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这些都奠定了许渊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根基。
师从钱钟书是许渊冲一生获益最多的事情。他认为钱钟书“贯通古今中外的才学,不但是前无古人,就是以后恐怕也难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
大一第二学期,许渊冲分到了钱钟书小组求学。那时的钱钟书28岁,只说英语不说汉语。他解释怀疑主义时说: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hing is a full-stop.(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点。)在许渊冲看来他不仅用具体标点符号来解释抽象的怀疑主义,而且问号和句号对称,everything和nothing又是相反相成,既得到了内容之真,又体现了形式之美。
在课堂上以及在之后的人生岁月中,许渊冲一直写信跟钱钟书先生谈论他译诗的思想动态和行动,钱钟书道破翻译的难处:“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而认为许渊冲的译诗是“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许渊冲得到了许多鼓舞。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将中国的古典诗词翻译成英法韵文以来,许渊冲一直坚持不仅翻译诗文,更要译出诗的意境,且译后仍能对仗工整,翻译出了许多音义双绝的精品。
他翻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sight.
他翻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正如他的老同学杨振宁说:“他特别尽力使译出的诗句富有音韵美和节奏感。从本质上说,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好的事,但他并没有打退堂鼓。”
随军翻译惊艳全场
20世纪40年代初,正是日本大举侵华之时,许渊冲一直遵循着父亲的教导,无心政治,对军队生活深恶痛绝。但他不曾想到,他成了大名鼎鼎的飞虎队(美国志愿空军大队:1941-1943年援助中国对日作战)的随军翻译。也不曾想到,这次随行激发了他对翻译更浓厚的兴趣。
在飞虎队的欢迎大会上,许渊冲翻译了“三民主义”: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惊艳全场。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袭,许渊冲因为之前出色的表现,被分配到昆明巫家坝机场的美国志愿空军第一大队。次年7月,飞虎队撤离中国。受赏识的许渊冲不愿赴美寄人篱下,回联大复学了。也正因为如此,1950年,没有赴美的许渊冲获得了赴法留学的机会。他在法国的巴黎大学研习文学研究,后来在法文上有所建树。
在西南联大的第四年(1942年),为了养活自己,许渊冲到联大附近的天祥中学教书。他说:“当时天祥中学,就是天下第一中学,学校里有7个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个啊。”在天祥中学的教师里,有为发展核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朱光亚院士,还有中国科学院池际尚院士等。
如果说西南联大的时光(1938年-1946年)是许渊冲“不逾矩”的8年,那么在天祥中学的时光(1942年-1947年)则是“从心所欲”的5年。天祥中学的校训是“紧张活泼”,当时的校长邓衍林解释说:“上课紧张,下课活泼。”
许渊冲喜欢“唱反调”:上课也要生动活泼,下课打球玩牌也要紧张认真。“那时,我们要怎么玩就怎么玩,师生打成一片;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充分发挥联大所学。”说起那段时光,许渊冲的眼睛都亮了。
“他们不懂”
如今,许渊冲说自己在“从心所欲不逾矩”地生活:“我这个年龄身体有点不正常了,不正常也是正常的。到了90岁,累了就睡,醒了就做事情,顺其自然。”
90岁以前,他每天都在北大的博雅游泳馆游泳。如今年过90岁,由于医院不予开证明,他被迫停止了游泳。他有些懊恼地说:“我其实还可以再游的,他们不懂。”
70岁前,他先后在解放军外语学院、北京大学外国语和国际关系等学院任教。70岁退休之后,翻译和游泳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
住在不到8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许渊冲对衣食住行要求不高。“老伴要我住得好点,但我搬不动了。我吃得很简单,但要吃我喜欢的,不喜欢的我坚决不吃。”
在访谈的最后,许渊冲的夫人照君女士说:“翻译这一行被人看不起,不算学科。我们有‘不如人’的感觉。许先生不因为小而不做,要把小做大。今天许先生做到了。”许先生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正如萧乾所言:“他成绩很大,没有浪费那些空白。”
许渊冲在翻译的“小”世界一做就是70年,狂傲、朴素、坚持。在与他拍合照话别时,我们赫然看到主卧的横幅上写着12个大字:“骄傲使人进步,自卑使人退步。”
据《北京日报》报道 日期:2014年8月27日
心译翻译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