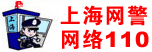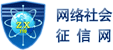傅惟慈,满族,北京人。1923年出生,1942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后借读浙江大学(贵州)。1947年转入北京大学西语系。1950年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留学生讲授汉语,并从事翻译。退休前任北京语言大学外语系教授。2014年3月16日逝世。已出版主要译作有德译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臣仆》,剧本《丹东之死》,英译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问题的核心》《密使》《长眠不醒》及《动物农场》等。
在翻译界,傅惟慈的名字与毛姆和格林二人连在一起,犹如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或者傅雷之于巴尔扎克。投身翻译六十年,译介欧美文学。傅先生为人所知的成就固然在他的外国文学翻译,很少人知道他的一生也是一部传奇。
喧闹的北京城有个安静的去处。避开新街口的车水马龙,沿着人来人往的赵登禹路轻轻一拐,走进一条名叫四根柏的胡同,很快就到傅家小院了。胡同其貌不扬,小而简陋。若不是因为来拜访小院里的傅惟慈先生,我不会驻足,更不会注意它如此安静,静到一只鸟从屋檐下飞过都触目惊心。胡同里的光阴如同谁家青瓦上的杂草,自在生长,每日迎着东升的太阳,在风里絮絮自语。
那些春来秋往的午后,傅先生都会坐在他那满是花草的小院里,备好茶水佳肴,迎接年轻的年老的、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们。院子里的桌子拼起来,简易的椅凳随意摆开,女儿们把自制的中餐和西餐摆上桌,角落里烤串的炭火烧起来,于是满院飘香,于是红酒啤酒茶水都满上,欢声笑语也满满的,溢出了小院。来这里的多半是文化圈里人,彼此相识不相识都能聊上几句翻译或者文学。畅聊很尽兴。直到起风的黄昏,树叶飘下来,灯光亮起来,宾客稀疏起来。热闹过后,留在记忆里的,是欢快的宁静。那些回到喧嚣生活中的朋友们,会记得这片刻的自在,惦记着不久后还会重逢。
傅家的院门总是敞开的,朋友随便来,随时走。聊得起劲,一起吃顿便餐,客人不觉得拘谨,主人不觉得怠慢。高兴就好。
春又来的时候,傅先生走了。他突然到另一个世界游荡去了。一直天真地以为这个有趣的老人会一直陪着我们。我们竟然忘记了他从来不肯停下脚步。
脚下如有风
他一生都在向往外面的世界。
孤寂的童年,被父亲囚禁在老北京庭院里,背古书、临字帖的记忆如此难忘:
“长昼寂寂,我竖起耳朵聆听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各种音响。卖奶酪和果子干的小推车,走进胡同里来了。车轮吱吱呀呀地由远而近,最后停在院墙外边。卖果子干的老武头拼命敲击两只小铜盏,声声敲到我心坎上。后来小推车走了,我又听到一阵阵鸽哨的声音。一群鸽子在不远的地方往返盘旋,哨声一阵松一阵紧。低飞时,连鸽子扑动翅膀的声音都清清楚楚传到我耳朵里。我欠起身,伸长脖子向玻璃窗外望去。我看到的只是一块被遮断的方方正正的蓝天,蓝得叫我心里发空。”
“父亲是大神,是我既无法爱又不敢恨的人。他的命运是卑微的我不能左右的——祝愿与诅咒都毫无用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这样威力无边的势力。”
他一生都在与这种力量抗争。
日历翻到1943年,“我已经在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北平生活了十余年。”当时他是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西语系学生。正是被青春晃得睁不开眼睛的年纪。艾芜的《南行记》、高尔基的《在人间》《俄罗斯流浪记》强烈地吸引着年轻的心,这个怀揣着文学梦的青年,“渴望走出家门,在外面广大的世界混迹于千百万普通人中间”。
早在入大学前就开始盘算出行计划,离开敌伪统治下的北平。
“我渴望光明,渴望自由。在北平大学里念书,生活虽还算惬意,但却感到窒息。1943年春节前十几天,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我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卖给了同学,又从家里要了些钱,提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一辆南行列车。火车驶出车站,我向灰色的古老城墙和角楼挥手告别。未来等待我的是什么,是个未知数。我只知道自己将要走进一个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上帝给了我眼睛是叫我看东西,给了我双腿是叫我走路。我刚刚迈出生活的第一步,今后我还要看得更多,走得更远。当时我的思想虽然还模糊不清,但在潜意识里,已经逐渐定出终生遵循的生活准则了。”
学校里的地下工作者详细介绍了投奔“自由”的路程。先买一张平汉路火车票到河南新乡,再换乘支线去沁阳,到洛阳,后又辗转到西安、重庆,再到贵州永兴,终于投奔到因战争迁至那里的浙江大学。一个内地流亡学生的辗转逃亡路有许多惊心动魄,他却总能找出乐趣来。“一个人走在莽莽森森的山路里,山间空无一人。我这个一向居住在大都市的人,感觉像是回到了洪荒的世界。当年年轻气盛,只想到能够入学读书的光明前景,对旅途艰辛,并不放在心上。”途中在重庆大学困居,遇到一家电影院正在放映施特劳斯的传记片《翠堤春晓》,“这是我在北平就迷醉的一部电影,片中穿插着华尔兹王创作的七八首名曲。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还够买一张电影票,于是毫不犹豫走进放映厅。电影放映期间,我如痴如醉地沉浸在优美的曲调里,把现实窘境抛在了脑后。”
回到校园生活一年多,日寇南侵,先锋部队已经打到贵州境内,浙大被迫停课。他也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1945年初来了一个好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结束,美军把反攻重点移至远东,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大批人员进驻中国,英语译员需求随之大增。5月下旬,一辆十轮大卡车把綦江202师考取译员训练班的青年军士兵接往重庆,其中就有傅惟慈。接下来,青年军士兵开始接受军事训练,学会使用各种武器,手枪、带望远镜瞄准的步枪、火箭筒、投掷手榴弹……就在马上要奔赴战场的时候,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消息传来没几天,我参加的战斗组织也宣布解散。我随着美国人回到昆明,领到一笔复员费,回到遵义继续读书。我的抗战梦从此结束。”
战争空耗了青春,却不想,辗转求学中英语水平的提高和偶然习得的德文,开启了他人生的另一场远行。
他说:“年轻时有过不少荒唐想法,一个是想当作家,另一个是想做流浪汉,浪迹江湖,玩味一下生活于其中的大千世界。十八九岁的时候,背着行囊,离家远行,多少是受这两种想法支配。年纪稍长,思想渐趋现实,才明白人生仍以温饱为第一要务,只好缩回乌龟壳,寻一份稳定工作,当了一辈子教书匠。虽然如此,小时候犯的痼疾,似乎并未根除,没有才气当文学家,退而求其次,于批改学生作业之余,我开始译书。翻译外国文学,既能从大师级的创作里品味人生,又满足了自己舞文弄墨的癖好。”
译笔藏万军
德国作家格林所以把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逃避之路》,是因为“不论我到各地旅行还是执笔写作,其实都是一种逃避”。对于格林在中国的知音傅惟慈来说,这句话同样适用。
从20世纪50年代起,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要踩一段钢索,战战兢兢,唯恐栽入深渊,万劫不复。而运动又来得那么频繁。开不完的会,学不完的政治,干不完的活儿(正业之外),打扫不完的卫生,且不言消灭“四害”时敲锣赶麻雀,站在屋檐下挥旗轰蚊子,大炼钢铁时上山砍柴,困难时期到郊外采树叶……他只觉得自己这个小齿轮随着一架庞大的机器无尽无休地运转。他不甘心只做机器,不甘心总受外力推动,他要夺回一点点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
“像一个拾穗者,我把被浪费掉的业余时间一分一秒捡拾起来,投入了文学翻译游戏。我做这选择只不过利用我手中几张牌的优势——会一两种外语。图书馆不乏工具书,我的工作又使我能接触到一些市面无法购到的外国文学书籍。这一游戏也需要一点独立思考,一点创造性。在全心投入之后,我常常自己暂时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在乌云压城的日子里,我发现玩这种游戏还可以提供给我一个避风港,暂时逃离现实,随着某位文学大师的妙笔开始精神遨游。偶然间,我会被大师的一个思想火花击中。我感到惊奇,人居然能有这样的高度智慧,而我生活的现实为什么那么平凡乏味?”
从“反右”到“文革”,傅惟慈曾无尽无休地受到批判,原因在翻译了几部德国文学作品。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在“大跃进”前后和“反右倾”运动间隙中偷时间译出的。后来的翻译家杨武能说,这部书翻译水平之高,使得“在重译或复译成风的今天,至今没有人敢动另起炉灶的念头”。亨利希·曼的《臣仆》,傅惟慈着手翻译不久就赶上“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的年月,完成时“文革”的暴风骤雨已快临头,稿子一直在出版社搁置了十余年才见天日。在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年月中,要认真译一点东西可真不容易,只能在风浪的间歇中偷一点时间,另一方面又惧怕舆论的压力,只好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段。他把要译的书籍拆散,夹在经典著作和笔记本里,在开不完的大小会和学习中间,偷偷窥一眼犯禁的东西,思索这个词,那个句子该如何处理。
“文革”前后出书不能或不愿署名,稿费极低或根本没有,他与董乐山等老一辈翻译家,甘愿在政治运动中受鞭挞,违心给自己扣上散播封资修思想的帽子,也舍不得丢下笔杆。他说:“总想在荒芜的沙漠上,种植几棵青青小草,与人们共享。”
“文革”来了,一切事情都出了轨,他的小小的翻译事业自然也翻了车。一搁笔就是十年。
噩梦过去,“我同不少历劫的人一样,发现自己居然活过来了。我突然发现,过去的许多清规戒律逐一消失了,便急忙拾起笔来,把一些自己比较喜爱、但过去一直被列入禁区的外国文学书翻译过来。一本天主教徒作家质疑教义的宗教小说《问题的核心》,一个灵魂永不安宁的天才画家的故事《月亮和六便士》,几部伴随我度过‘文革’中苦难岁月的惊险小说。直到1990年,我还和老友董乐山共同译了《基督最后的诱惑》,据说出版后引起了一些争议,很难再版了。我的翻译生涯至此已近终结。时代变化了,过去那些热心在文学作品中游历大千世界、探索灵魂奥秘的读者群日益稀少。文坛冷落。我也决心封笔,不再玩这一文字游戏了。”
牌戏人生的乐趣
印象中,每次见傅先生,他都声音洪亮,谈兴很浓。来客总会不由自主跟着他的话语神游。沉默的间隙,猛然发现,他高大的身架陷在椅子里,有些别扭。两条长腿、一双大脚委屈地缩在那里,衬得桌椅那样小。只在告别的时候,他才费力站起来,送你几步。这双曾经满世界溜达的大脚,再也不能健步如飞了。
常去做客的朋友说,这些年几乎是眼见声如洪钟高高大大的傅先生,一点点衰老下去的。生死并不是他畏惧的。女儿说他是个“坚决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惧怕形神的消散。2007年的一天,他在报上看到医疗研究机构接收公民捐赠遗体的消息,立即与老伴一起跑完各种复杂手续,签下了遗体捐赠书。他对女儿们说,醒不来的那一天,直接找车拉走了事,不用举行任何仪式。
聚会中,那些“老愤青”们同他谈古论今指点江山,小“粉丝”们一脸崇拜围坐他身边。人们只感受到他智慧的光环,很少留心,他在什么时候坐在角落里沉默,或者回到了屋里。那是他疲惫的时候。
晚年的傅先生其实一直在与时间和衰老抗争。那是他一个人的战争。
他是中国最老的背包客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还没有旅行概念的时候,他已经利用教书之便,漫游欧洲了。甚至在82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大街上骑自行车穿行。在中国,他喜欢一个人,背着小包,寻找人烟稀少的所在。或是僻远的乡野,或是一个边贸小镇,常常随遇而安,只根据兴致所至。那时候他扛着一个胶片机,浪费了许多胶片,也拍了一些行家颇为赞赏的照片。他把那些异域的天空,偏远的街巷,古老的画面都冲洗出来,挂在屋里抬眼就可以望见的地方。
2009年摔坏了胯骨,八十多岁的人了,动手术见效快,却很危险,医院建议回家吃药静养。女儿们明白,这就意味着他接下来的日子将要在床上度过,这对于一生追求自由的老父亲来说,无异于一种囚禁。冒着风险,女儿们签字,把父亲送上了手术台。
手术很成功,87岁的傅惟慈又站起来了。天好的时候,兴致来了,他会骑着电动三轮车上街,逛胡同,逛后海,甚至一个人跑到前门。我猜想,他倔强的白头发肯定在风里自由地欢呼。但是我永远不知道这些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会不会想起七八十年前,在后海的祖宅里,被父亲关在书房里读“子曰诗云”的童年?或者想起穿越大半个中国寻求自由的青年时代?想起曾经走过的那些偏僻荒野和异国文明?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去想,沉醉在自在出行的快活里?无论如何,他的双脚仍然没有束缚,他的世界没有变小,真好。
他一直保持老派文人看报的习惯。家里订的报,他要第一个拿来看。看到有趣的新闻,还要讲给女儿听,喜欢的文章,甚至兴致勃勃地念给她们,好像女儿还是当年那个读书的孩子。许多没有客人来访的日子,他总忍不住唠叨自己年轻时那些“老皇历”。
他对一切新鲜事物好奇。iPad迷你上市,他买来玩,听说有好书,他找来看。遇到喜欢的,从不吝惜夸赞。前两年喜欢上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自掏腰包买了一二十本,逢人就推荐。不知什么时候《中国好声音》看上了瘾,买来光盘,一期一期地看。有时朋友来了,他兴致勃勃地叫上朋友一起看。这个爱好古典音乐的资深老乐迷,对流行音乐并无偏见,如同他的翻译既有严肃文学,也偶尔涉猎通俗小说一样。也许他从中看到了百味人生,也许这是他与这个世界保持联系的方式,是他唤起正在被时间侵蚀的生命热情的努力。无论如何,女儿们说,这个热闹的节目,傅先生看得很快乐。
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去年年初见他时,他高兴地念叨,这一年有三本新书出版:新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增订本《牌戏人生》和《傅惟慈译文自选集》。一本是曾为他赢得声誉的德语译作,一本是自己的人生故事,一本是他翻译道路的回顾。《傅惟慈译文自选集》需要核对样稿,体力不济,他不服气,拉上女儿来帮忙,一个人念原稿,一个人核对,累了交换一下。在这被迫的朗读中,女儿发现原来老爸的文字这样生动迷人。
客人来了,女儿们觉得轻松,因为不用听他唠叨那些陈年往事,不用因为心不在焉而惹他不高兴。她们对眼前的他太熟悉了,以至于对他的过去提不起兴趣。客人们却不同,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这时候,陷在椅子里的傅先生是快乐的。他声音明朗,谈吐有趣,思维敏捷,很容易让人忘记他的年龄,忘记他会疲惫。他也乐于忘记这一切。朋友们的来访,是他与这个世界联系的重要部分,他们带来的消息,仍然开拓着他思想的疆土。走天下路,结交天下朋友。这一习惯似乎在他二十几岁闯荡世界时便已形成。过完九十大寿这一年,他从街上“捡”回两个朋友。这夫妇两人从门前过,被傅家院子里的花草吸引,驻足张望,傅老招呼他们进门,于是成了朋友。后来夫妇二人又带来一位爱好中国文化的德国人。谈起德国,他的思绪又回到那些他曾经用脚丈量过的街道,回到魏玛的歌德、席勒像前。
因为喜欢印度政治家尼赫鲁的话:“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傅先生在《牌戏人生》里,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我手里的牌都将打尽,也许最后的一张——寿命,也随时可能被发牌者收去。但目前他还在我手里,我正摸索着这张牌的玩法,我要玩的自在一些,潇洒一些,我也希望我玩的游戏能与人同乐,使那些赞赏我的游戏的同道与我共享乐趣。
来源:人民网 日期:2014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