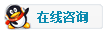在中国,研读法语的人相对英语来说要少得多,所以了解何如先生,读过何如先生译著的人也许为数并不很多,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何如先生译著的价值。而且长期以来,何先生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默默无闻的工作,他一直参与《毛泽东选集》的法文本翻译,而且是该书法文版的最后定稿人。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大理解“最后定稿人”这一说法的份量,然而在当年那种政治氛围中,这应该视为对何如先生中法语言功力的最权威的肯定和最高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说,当年的中国法语界,能够担此重任的,何如先生应是不二人选。
何如先生是翻译家,也是诗人,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位诗人翻译家。他既能写中文诗,也能写法文诗,他用法文创作的诗篇曾经惊动巴黎诗坛。何如先生酷爱中国古典诗词,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理解力和敏锐的感受力,并且谙熟古典诗词的音韵与格律。与此同时,他对于法国语言词汇的变化和发展,法国诗歌创作各个流派的背景和代表作家有着深入而独到的研究,熟练地掌握了法国诗歌音韵和句法的特点。正是因为对于中文和法文的运用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何如先生才能够进入汉诗法译这项最艰巨的翻译领域,辛勤劳作精心耕耘,并且获得了丰收。他翻译过很多中国古典诗歌,当代诗歌以及当代人写的旧体诗,其中就有毛泽东诗词三十余首。
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想必都有深刻的体会,诗是最难翻译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诗歌的语言含蓄精炼,富有音乐感,更重要的是,优美的诗篇所包含的某种境界,也即人们常说的“意境”,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翻译家可以把一首优美的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法文或其他文字,文字可以同样优美,而且读起来或悦耳动听或铿锵有力,但是诗味可能相去甚远,因为仅有优美文字的译文未必能表达出原诗的意境。翻译诗歌,形似已属不易,神似则更困难。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语言功力之外,对原诗诗意的深刻领会和灵活把握应该是更加重要的。
这里仅举一例。杜甫的代表作中有一组七律《咏怀古迹》,全诗共五首,第三首是咏王昭君的,其颔联曰:
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塚向黄昏。
古往今来,人们对这一联诗句评价极高,称之为千古绝唱,寥寥十四个字,写尽了昭君寂寞凄苦的一生。这句诗若按字面实译的话,其中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够在法文中找到相应的词,但是这样译出来的法文诗淡如白水,与原诗的魅力不可同日而语。而何如先生的译文是:
Fuyant le palais pourpre aux voeux du désert sombre,
Elle a sa tombe verte au couchant éternel.
译文不仅像原诗一样,概括了昭君悲剧的一生,而且基本表现出了原诗的神韵。杜诗中的“一去”,何先生选用了法语动词“fuir", 颇堪玩味。再者,何先生在译诗中还使用了“aux voeux”和“au couchant éternel”两个词组,读起来令人不胜伤感,仿佛看到了哀风夕阳下的那座孤零零的青塚。我常常揣想,何先生翻译这首诗的时候,想必是在夜深人静之际,他在冥想之中,眼前辉映着塞外荒原上的落日晚霞......
何如先生的法文译诗可以说已入化境,博得了通晓诗歌的法国友人的高度评价。人们赞赏他完美的表达手法,完美的韵律,译诗清纯而又含蓄,简直就像是用拉辛、雨果、兰博、瓦勒里、阿拉贡的语言直接写成。把何如先生的译作与法国诗坛巨匠相提并论,这是何如先生译作的法国知音发自内心的赞叹,这种赞叹是对他译作最丰厚的酬报。
何如先生是我的老师,我有幸亲聆他的授课,受益匪浅终生难忘。何先生逝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回忆起来犹在眼前。我与何如先生并无私交,有限的几次个别接触,大多是听他讲述翻译诗歌的感受。记得有一次何先生对我这样说过,他常常几乎熬一个通宵,也只能敲定一两句,而自己还未必满意。何先生自述翻译的甘苦,使我联想到宋人《诗人玉屑》中的一段话:“诗,最难事也。吾于他文不至蹇涩,唯作诗甚苦。悲吟累日,仅能成篇,初读时未见可羞处,姑置之;明日取读,瑕疵百出,辄复悲吟累日,反复改正,比之前时,稍稍有加焉;复数日取出读之,疵病复出;凡为此数四,方敢示人,然终不能奇。” 何如先生的翻译就是这样精益求精,力求完美,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译作才能达到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法国政府曾向何如先生颁发一枚勋章,以表彰他对中法文化交流的卓越贡献。据说这类勋章是有等级高下之分的,但是我一直弄不明白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不过我总以为,在我听说过的这类勋章里面,何如先生的这枚勋章应该是含金量最高的。
来源:欧洲时报周刊 作者:王聿蔚 (本文系作者关于汉诗法译专论的导言部分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