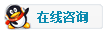| |
|
主讲人 宋明炜,美国卫斯理大学学者,文学研究者 摄影/高寒凝 |
今年,刘慈欣的《三体》英文版即将在美国上市。这个让科幻迷欢呼雀跃的消息,真的意味着中国科幻即将走入美国主流社会吗?学者宋明炜近年在美国学界致力于研究中国科幻,他曾在一部有关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中,把其中关于中国科幻章节定名为“红星照耀美国?”(该名来源于韩松所写的科幻小说《火星照耀美国》)。这个让美国人感到惊悚的名字,是否预示着中国科幻在美国的成功呢?不妨听听宋明炜细说端详。
主题:“新星科幻大讲堂”—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科幻的研究
我们觉得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科幻的认识,滞后一百年
2010年,王德威老师所在的哈佛大学要和复旦大学举办一个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会议,我就跟王老师提议,能不能把科幻的内容也放进去,特别提出要把刘慈欣请来。通过严锋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最终没能请来大刘。
但是我见到了飞氘和韩松老师。在那一次会上,飞氘和韩松的发言是整个会议的最高潮,飞氘讲了四个故事,跟鲁迅还挂起了关系,把科幻和在座的大学者的兴趣都连了起来。就像通电一样的,现场一片电波,有教授当场就说要让自己的研究生去写关于科幻的论文。
现场还感染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加州洛杉矶大学教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胡志德老师,他刚好接手香港一个叫《译丛》的杂志,是中国文学向海外翻译推荐作品的大本营似的平台。胡志德老师跟我说,咱们搞一个科幻专题怎么样?
我们觉得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科幻的认识,滞后一百年。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科幻的认识停留在晚清的十年,就是1902年到1912年的十年之间。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专题变成晚清和当代的对应。中国晚清和当代有很多对应的地方,社会都在巨大的转型当中,晚清出现现代的媒体、报纸,和现在出现网络和微博虽然不是一回事,但在打开不同的传媒面方面有类似的认识。晚清的科幻中有一种对于未来的焦虑和想象,当代中国科幻也是这样的,虽然呈现的面貌是不一样的。
晚清的作品里面,我们选的是徐念慈的文言小说《新法螺先生谭》、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另外还有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等等。跳过一百年,接下来的作品包括刘慈欣的《乡村教师》、《诗云》,韩松的《乘客与创造者》,夏茄的《关妖精的瓶子》,飞氘的《魔鬼的头颅》等。我同时也开始写一些英语的相关论文发表。
这个时候吴岩老师主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在美国理论研究杂志《科幻研究》的一个中国科幻专号,也在这一年发表。这两个专号在同一年出来之后就引起了美国的中国研究界的兴趣。在此之前,美国的中国研究界是没有中国科幻的位置的。今年我收到很多信,很多学生开始用科幻做自己的博士论文,这就意味着这个领域要小火起来了。
我写过一篇研究论文是关于中国科幻发展有过的三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晚清的十年;第二个是20世纪70到80年代;第三个是90年代末到现在持续的浪潮。对这三个不同区域的研究,美国学者主要集中在晚清,这跟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中有晚清热有关。中国现在的未来如果还是梦想的话,那么晚清的中国梦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另外,70、80年代的研究也在不断有人介入。我希望对当代的、正是上升阶段的作家的关注还要加强,目前美国只有我一个在写学术论文。我的老师王德威在自己新的论文中倒是给了中国当代科幻两页的篇幅,讲到了刘慈欣和韩松,还没有发表。他也给我在哈佛当代文学新史上一个篇幅来写中国当代科幻。
中国科幻能不能在美国火起来,客观地讲,我觉得比较难。美国其实不是一个很接受翻译文学作品的国家
我觉得特别要提到一个重要的、中国科幻在美国的推手是刘宇昆,他是一个写得很好的科幻作家,在科幻的这个商业化的流通渠道里很有影响力。他翻译了很多中国科幻作品,他的翻译是一种很通俗的、能够为现代读者所接受
的风格,不像我们翻译徐念慈的作品,读起来是比较典雅的那种。他更重要的工作是从前年开始翻译《三体》,这部小说应该今年会进入美国,美国人就该知道三体人的存在了。
大家当然关心中国科幻能不能在美国火起来,客观的讲,我觉得比较难。美国其实不是一个很接受翻译文学作品的国家。可以这么讲,很少有外国翻译到英语的作品变成畅销书的。我知道的就是艾柯的《玫瑰的名字》,那是个特例,而且主角还是个英国人,沾了福尔摩斯的光。至于科幻界,我很想买一点翻译的别的国家的科幻小说,但是书店里很少。比如《日本沉没》是有的,但是日本的科幻小说介绍过来的也就那么几部。阿根廷是因为有博尔赫斯,他是对先锋派影响最大的作家,因为他的原因,阿根廷有一些科幻作家在英语中有翻译和被接受,但是也不火。
我预感到中国科幻如果要美国化、通俗化、市场化,那么就会失去很多过去好的东西,非常尖锐的有意义有力量的东西会被稀释掉
大家一直在讨论主流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问题,包括刘慈欣也在讨论是否把科幻界限分明地放在通俗文学里。美国科幻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世界的,二战以来,科幻杂志为了卖杂志组织读者俱乐部,培养粉丝,所以科幻有一个像自己的社群一样。在书店里科幻是被列入science fiction(科幻),不是literature(文学),是自己单独的一个门类,这也造成了文学和科幻之间一个非常大的鸿沟,包括得诺贝尔奖的多丽丝·莱辛,她写过几部科幻作品,她感到很悲哀,人家都说你这样的作家怎么会去写科幻作品?
但我觉得在中国当代,至少从我刚开始看韩松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看到中国先锋文学的精神的延续,有一种对陈规的挑战,不像美国科幻。很多美国科幻并不好看,因为它是跟着陈规来的,包括出版商也觉得你要符合陈规,电影也是一样,才能够被接受、卖钱。什么样的电影会让大家喜欢呢,就是要认同里面的东西,大家就会喜欢。如果电影否定你认同的价值,就是所谓有争议性的电影,就不会有人愿意投资。科幻处于这样的模式当中,他不断给你确认原有的价值的时候,就失去了对社会产生反省和不断推进的能力。
我觉得这种能力在阿西莫夫那一代,是特别超前的,预见到很多社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表述都是有先锋性的。中国科幻给我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这种感受慢慢在变弱,我感到大家有一种要市场化的倾向。我预感到中国科幻如果要美国化、通俗化、市场化,那么就会失去很多过去好的东西,非常尖锐的有意义有力量的东西会被稀释掉。
还有就是认同的局限和差异性。不知道大家看科幻是为了什么,得到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我觉得好的科幻给我带来的快乐是差异性,最伟大的科幻是在一个寻常的世界中与一个他者、一个真正意义上不同的东西的相遇。我举过一个例子,正常生活中场景,普通一个人去上班,到了办公室之后不是掏钥匙开门而是手一碰门,墙就消失了。
19世纪的时候美国出现很多科幻作品,有一个小说叫《last day of the republic》(《共和国最后的日子》),写当时去美国的中国华工把美国占领了,把美国变成了中国,就是作者对中国这个不同的族群的认识,有种族主义的东西在里面,他对中国有一种认识的差异。我说这个的意义在于,陈楸帆的《荒潮》,你开始看就会觉得特别真实,那种气氛和中国的地方官文化、家族文化很真实,在这种东西里面写到了一种真正差异性的东西,我私心里觉得可以写得更大胆一些。
这里面带有一种对原有认同的挑战,也就是我们看一个科幻电影如果只是加强了我原来对于英雄主义的想法,这个电影就是一个娱乐和消费,满足快感。但是如果它挑战了你的认同,给你带来一种差异性的感受,这个差异可以是族群、性别、人与非人,甚至就是对自己的个体体验的挑战,那么是很重要的。当年读刘慈欣、韩松打动我,是因为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烈的。这些年我觉得有一种稀释的感觉是,大家开始建立一些规则和陈规了。我觉得永远要保持对陈规的警惕,要保持一个自己的风格还是意识上的认同?你要永远知道只要是认同就有局限性,你要知道真正具有活力的东西一定在认同之外的差异上。科幻这种文化的力量在哪里?它永远都是指出人类认同的局限性,以差异的方式提出一种理想,但是同时又对这个理想保持一种警惕,这就是最高的境界了。
回到科幻跟主流文学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在这里面。
来源:北青网-北京青年网 日期:2014年1月24日 作者: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