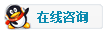译过《洛丽塔》,出过长篇小说,到美国后从头开始干服庄。颀长身材、利落短发、姿态优雅,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望京一个咖啡馆见到于晓丹时,她给人的时尚感觉恰如她的职业——“设计师”。其实,于晓丹这个名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圈“红”过一阵子,她翻译了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经典小说《洛丽塔》,是该书在国内最早的译本之一;她写过长篇小说《1980的情人》,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年代。文学道路上一帆风顺之际,她却放弃一切,从零开始,在国外的服装设计界打拼,最终带着顶尖内衣设计师的名头回来。想起当年在纽约街头的迷茫、困惑,于晓丹自己都说:“感觉不像是真的。”
放下文学梦
上世纪80年代,20岁出头的于晓丹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外国文学评论》做编辑,没多久就开始着手翻译《洛丽塔》。她的一位朋友回忆:“那时候她住在北京朝阳门南小街后拐棒胡同社科院的宿舍,是筒子楼里的一个小间,冬天屋里非常阴冷。她翻译得很费劲,因为其中充满双关语与典故,需要借助词典并请教老师。”《洛丽塔》是翻译界里公认难译的书,“想找人校对都找不到,老专家都不敢看”。一年之后,这个倔强的女孩完成了这个工作,出版后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继纳博科夫之后,于晓丹又翻译了雷蒙德·卡佛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写了小说《1980的情人》,编过《玫瑰树——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英国卷》等书。刚开始崭露头角,她突然决定到纽约去。“去之前做的还是文学梦,想着学了那么多年外语,怎么能不去外面感受一下?”她想,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再翻译纳博科夫和卡佛,肯定会更准确些。“可在美国东部转了一圈再踏上曼哈顿岛后,杂念就多了。上世纪90年代的纽约,是个容易让人有梦的地方,而且只要你坚持梦想,多半就能开花结果。我就觉得换一种生活亦无不可。当时我甚至有过去上高尔夫学校的念头。”
这个瘦弱的女孩思索很久,最后选择了去学内衣设计。“在国内,像我这样没有任何绘画天赋的人,怎么敢进美院或设计学院这种高门槛的地方?尤其工作后,到了一定的年纪,改学一门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无异于痴人说梦。可到了纽约,也许是艺术和实用的界限不像国内那样分明,这样的梦似乎也并非遥不可及。”
绘画是最大的绊脚石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服装设计这一行要想表现杰出,单有勤奋可不够,还需要天分和运气。于晓丹曾经为学业熬夜、掉泪,崩溃到几乎想退学,所受的苦不堪回首。
那个暗淡的岁月,她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记述道:“正式进入纽约时装学院以后,我第一学期选了10门课。每周5天,每天从早上8点进教室,到凌晨一两点才能做完作业躺下。这种疯狂在这所学校十分正常,要想修完学校规定的学分似乎只能如此。老师说,这个节奏基本上就是这个行业的节奏,如果你不能适应,就说明你不适应这个行业,趁早退学或改换专业。我那一班开学时近40人,一周后就走了1/4。”
对于“半路出家”的于晓丹来说,绘画是她学习中的一块绊脚石。“布料学,染、织等课程,我没什么问题;立体裁剪课,我上手很快,成绩也最好;可绘画课就没那么顺利了。我的图太丑,设计基本无理念可谈,上绘画课对我来说简直是煎熬。班上还有两个绝顶聪明的越南女孩,完全就是天才,每次大家等着看她们的绘画作业,就像今天翘首以待顶尖的时装发布会一样,连老师都禁不住带头鼓掌。可轮到我打开作业时,老师就面无表情了,眉头紧得让我战战兢兢、语无伦次。无论我多么努力,始终拿最差的成绩。这样上了一个月,我的神经几近崩溃——我开始失眠,莫名其妙地大哭,甚至在课堂上落泪。”
“有一天上完绘画课进了立体裁剪教室,老师看到我哭了。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实在坚持不住,想退学了。她立刻绷起脸说,‘胡说!’继而跟我讲,‘要是你相信我,就再坚持一个月。绘画是可以学的,如果一个月后你还学不好,我就不再劝你’。我看着她,点了点头。我信她,坚持到了现在。”
时尚行业并不只有光鲜
从毕业到现在,于晓丹在内衣设计行业已经干了10年。她说:“这10年的经历实在太特别了,它把我的性格和意志重新打磨了一遍。”
“这是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你的工作是由各种‘最后期限’组成的,每个人都高度紧张。更可怕的是中间环节很多,光布料从提供到加工、从染到印就有无数环节。刚开始我在一家小公司工作,老板如同太上皇,不受任何约束,员工没有任何发言权。就拿工作时间来说,我最长的时候一天做18个小时,半夜2点回家,只休息了4个小时,就又被召回公司。由于压力太大,这个行业的老板都有‘病态’倾向。我遇到过一个每天要服抗忧郁药物,骂起人来又要服抗兴奋药物的老板,曾被他吼得躲在储备间不想出来。”
不要以为进了大公司情况会有所变化。服装设计界竞争“惨烈”,在哪里都可能被淘汰。“我曾被一家大公司挖走,可不到一个月又被解雇。设计是服装界的灵魂,可一旦产品出问题,所有的责任也会一股脑儿推给设计师。因此,能干二三十年的设计师,都是不结婚、不生子,可以不眠不休地跟工作搏斗。 我认识一位很资深的设计师,她没有婚姻和子女,头发已经掉光了,只能戴假发,每天提着行李箱带着资料上下班,恨不得把办公室搬回家。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这个行业扎下根来!”
于晓丹说:“时尚界看似风光无限,但T台后的服装业却相当残酷,更无鲜亮可言。淘汰率之高、之快,诱惑之多,是我这颗曾经装满文学的脑袋无法想象的。”
但是,“设计会让人上瘾”,“看到自己的设计出现在商店里,你会非常兴奋”,“它给了我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满足了我很多‘浮生’的欲望。比如我喜欢跟人打交道,这份工作给了我机会与各种肤色的人合作:我们的工厂设在印度、巴基斯坦、中国,供货商也来自世界各地。再比如我喜欢逛街,现在这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每天遇见的人和事,也许不够深刻,但五光十色,让人难忘。”
内衣要穿给自己
说起“内衣”,于晓丹说每个国家的人听到这个词反应都不一样,中国人会马上想到文胸和内裤;日本人会有点不好意思;美国人则多半会联想到著名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的T台秀。
“穿内衣是为保护我们的身体,更是为美化身体。可惜现在我们很多女性不重视内衣。”随着经济发展,如今很多人的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但内衣,却还没有得到科学对待。 “很多人选择内衣看重的是别人‘看着怎么样’,而不是自己‘觉着怎么样’。”于晓丹强调说:“‘内秀’才是内衣的基本品质。其实这又何尝不是生活的本质。”
与于晓丹聊天很轻松,她的中文里没有夹外语,也没有刻意学美国人夸张的肢体动作和表情。身上的衣服是小店里买来的,没有多余配饰,简练精巧中自有一种味道。回顾这10多年的经历,于晓丹说,从空白开始,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份勇气,她很高兴自己能坚持下来——当你真正喜爱一件事时,你所要做的,仅仅就是对理想的坚持。
来源:荆楚网-楚天都市报 日期:2012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