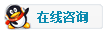挂完博客外出上课。晚间回来得知莫言获奖。我暗自庆幸:莫言君获奖采访轮不到我了。岂料记者仍不依不饶,追问为什么莫言获奖而村上没获奖?是啊,为什么?要知道,诺奖从来没有为什么,有也要等到50年后。不过细想之下,以上三点获奖理由之中,第二第三点应该没问题,也容易为瑞典学院十八位评委所认可。问题可能出在第一点,即村上的语言特色未必引起太多注意。这意味着,村上独特的语言风格在英译本中可能未得到充分再现。这又为什么呢?想起来了,记得翻译过《挪威的森林》和《奇鸟行状录》的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说过,村上那种脱胎于英文的语言风格是一把双刃剑:“村上那种接近英语的风格对于一位想将其译‘回’英文的译者来说这本身就是个难题使他的风格在日语中显得新鲜、愉快的重要特征正是将在翻译中损失的东西。”说白了,回娘家时娘家人不稀罕了。这当然怪不得村上,也怪不得译者,所谓宿命大约就是这样的东西。
另外,看过英德译本的大学同事和朋友告诉我,简洁固然简洁,但感觉不出中译本那种隽永微妙的韵味。而这分明是村上语言风格的另一特色。已故日本著名作家吉行淳之介曾经予《且听风吟》这样的评价:“每一行都没多费笔墨,但每一行都有微妙的意趣。”莫非英德译本把“微妙的意趣”译丢了?有一点倒是事实:尽管村上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余种语言,涉及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但那里的读者和评论家几乎没有对作品的语言特色给予明显的关注。而若关键的瑞典学院评委们也没给予明显的关注,那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最后补充一点。表面上看,莫言是土掉渣的乡土文学作家,而村上是洗练的城里人,处理的也是都市文学题材足可见证“城乡差别”。但骨子里两人又有相通的东西。莫言受《聊斋志异》影响较深,村上受《雨月物语》影响较大,而日本的民间故事集《雨月物语》又深受《聊斋志异》影响,可以说是日本版《聊斋志异》。一个主要表现,是两人都有不少作品主人公自由穿越于阴阳两界或此岸世界与彼岸之间,都具有对于现实的超越性,从而为探索通往灵魂彼岸的多种可能性开拓出广阔的空间。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林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