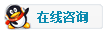编者按
今天,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是本报大型系列策划“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之七。
在这里,本报“重估”改变一下视角,把中国当代文学置放在世界文学整体格局里,从文化交流、译介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处境。这个处境,即无论当代文学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这个成绩都不等同于在世界上产生了等量齐观的影响。翻译与介绍,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唯一桥梁,今天看来,像独木桥,能够通过这个独木桥在西方世界产生影响的,只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因此,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误读与有意的误读,都不可避免。
翻译与介绍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被称为汉学家。汉学家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少之又少。中国了解西方文学有百年的历史,而西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这种了解的不对等,是许多中国作家所忽视的事实。也正是这种不对等,才使中国文学长久地被世界所忽视。也正是因为忽视这种不对等,中国作家才对诺贝尔文学奖耿耿于怀,对顾彬的言说如芒在背。中国作家内心里,充满了急于成为世界作家、得到普遍认同的焦虑。了解了这种不对等,就会发现,文学真正地走向世界,路比想象的要长。
随着经济成就的不断取得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国家,中国文化有了走向世界的契机。文学作为民族和国家的精神窗口,该展示怎样的内涵和形象?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不能以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为条件,而是要深刻地表达中国,为世界文学提供精神和思想资源。这是中国文学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标。
中国作家生活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埋头写作的时候,应该直面并思考这样的问题,为自己的写作找到一个参照系。
在随后刊出的系列访谈里,本报将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本报在大型系列策划 “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推出之始,便集中讨论过有关著名汉学家顾彬的一些争议性话题,但是,顾彬毕竟只是众多汉学家中的一位,他的观点和看法,且不论是否被媒体扭曲,但毕竟也仅仅是他的一家之言。那么,从整体来观察,汉学家们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汉学家们又是怎样一个群体?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些问题恰恰并不被大多数人所关注。因此,本报希望找到一个具有沟通性的视角,以第三方的姿态来深入了解汉学家这一在当今中国越来越被关注的群体。从去年12月开始,本报记者在南京、北京、上海、沈阳等地,先后专访了南京大学教授许钧、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史国强等四位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比较文学研究专家,借由他们带有参照性的观察,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海外研究视角,更加客观地认识汉学研究以及汉学家们。
中国了解西方文学有百年的历史,西方了解中国文学只有二三十年,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汉学家的历史已经有数百年,最著名者包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事实上,汉学研究包含众多领域。汉学家,顾名思义,也就是专门从事汉学研究的专家,研究与中国有关的内容,是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化。被称为汉学家的人是指那些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者海外华人。
许钧、陈众议、谢天振、史国强等四位教授都因研究工作的关系,与许多海外汉学家、翻译家有频繁的接触,在他们看来,海外的研究者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学的了解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误读和隔膜,不过,中国文学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虽然没有统计过西方汉学家的人数,也没有看到过类似的统计,但以我的接触和了解,专门从事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汉学家其实并不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表示,他近来十分关注海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也常常思考当下的中国文学究竟应该如何评价。 “汉学家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各有不同,关键要看他们各自主攻的方向是什么。一些汉学家喜欢把当下的写作状况跟‘五四’时期相比较,这样的比较并不科学。鲁迅那一代人是开拓性的,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王国,他们无论是审美或是认知都继承了19世纪最好的外国文学,而且那个时候整个文学的氛围都不同于当下。如果非要将‘五四’时期拿来与当下作比较,那对现在的作家自然会有比较大的争议。 ”
而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则表示,他接触过很多海外的翻译家,而根据他从交往中得到的反馈,海外翻译家和研究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持肯定态度的人越来越多。 “我接触的汉学家和翻译家,都是比较肯定中国当代文学的,蛮积极地在介绍我们当下的文学。海外对我们的了解还不够,他们认为还有很多值得介绍的作品。我认识一位韩国的女作家,她放弃了自己的创作,全心投入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工作。因为她感觉到中国的文学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在韩国的读者越来越多,她很看好中国文学的发展前景。莫言所有作品的韩文版都是委托她翻译,莫言还专门去过韩国。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有很好的发展势头的。 ”谢天振认为,由于中国日益强大,全世界的目光都转向中国,中国的文学同样也越来越受到瞩目,因此,汉学家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现在学中文的外国人不断增加,能够说得好中文的也很多。如果这个势头持续下去,外国对中国文化、文学就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那样,他们对中国文化、文学给出的判断就会不一样。 ”
即便如此,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史国强说,中国小说在国外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所以也没有固定的读者群。以美国为例,无论是书店或是旧书摊,几乎见不到中国翻译出去的小说。王安忆的短篇小说集见过一本,上面有她小时候的一张照片,其他小说家的作品都没见过。他们有一家Barns&Nobles图书连锁店,关于中国的东西,写风水的最多,整整一个专柜。美国人开始讲究迷信了,不读你的小说,你还有什么办法。
顾彬写中国当代文学只写到1992年。今天的汉学水平远远不及汤若望的年代。他们的观点不能高估,但值得尊敬
自从顾彬被中国大众媒体 “包装”成“顾大炮”后,他便成了公众眼中汉学家的代表性人物,进而片面地认为,汉学家对当下文学和当下作家的评价都是否定性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变成了“外来的和尚爱批评”。
陈众议说,顾彬的观点其实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能代表西方评论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他说:“顾彬先生,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也不是主攻中国当代文学的。当然,他是位严肃的汉学家,但他的主要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了解和研究程度不能说是很全面、很深入。单以目前年均上千部长篇小说论,恐怕没人敢说他对中国文坛了如指掌。同时,顾彬的主要立足点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一干巨人,所取法的批评范式也主要是较为正统乃至相对传统的西方文学理论,如19、20世纪的社会历史批评,故而对他的观点我们只能姑妄听之。 ”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史国强提出,从顾彬的文章来判断,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是很有限的,“我是说,他阅读汉语的能力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提出的观点,大半都是不言自明的东西,有些推理有时也莫名其妙。比如,他写王安忆继承了张爱玲的一些传统,所用的证据是 《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的标题,其‘样板显然是《倾城之恋》’,又说‘王安忆叙事模式很多来自张爱玲笔下扭曲的女性心理’。不知是在抬高王安忆还是抬高张爱玲,还是在陈述一个不一定是事实的事实。下面,顾彬又写道:‘由于王安忆始终不厌其烦地从自传角度解读自己的作品,使得正确评价她卷帙浩繁的作品变得十分困难。 ’再有,本来是写王安忆,还要捎带一句张贤亮,‘像张贤亮这样对女人怀有荒唐想象的男作家难道真有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面? ’张贤亮平白无故被贬了一句,而且无法解释。其实,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在《朗读者》之下。至于说‘王安忆的写作是神经质的,根本不能停笔’,而且‘始终在写同一样的东西’,就更是匪夷所思了。据此,至少可以说顾彬是不大了解王安忆的。更有趣的是,顾彬写中国当代文学,到1992年戛然而止,对于之后出版的《废都》及马原等作家仅在注释里提了一笔。总之,不应过高地估计他的判断。 ”
“有人把他称为汉学家,但他怕是不能和利玛窦、汤若望那些人相比。对于中国人的事,没有几十年的真功夫很难说出一二三来。连费正清写的《伟大的中国革命》,读起来也不是滋味。 ”史国强借用鲁迅在与姚克的通信里说到赛珍珠时的一句话:“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 ”他说,“鲁迅的话有道理。外国人写的书毕竟是给外国人看的。他们的判断不一定准确。顾彬说中国当代小说在国外取得成功,进入了每一家读书俱乐部;葛浩文说每年大概出版三五本的样子,绝对不畅销。两人都是汉学家,你不知道该相信谁。 ”
另一方面,南京大学教授许钧认为,任何对国外文学的引进或者说翻译,必须有一种参照,而这种参照就是中国的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对于汉学家们的观点,他抱持着比较积极的态度,他说:“顾彬之所以敢说出那些结论,首先说明他在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他在关注中国文学,关心中国的文学创作。他和我们的作家其实有很多交流,而真正的文学交流应该是从文本阅读开始,从文本的思想对话交流开始。所以,我想,第一步,面对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不用急着接受,也不必急着反驳,应该让我们中国的文学真正走出去,让更多的人来关心中国文学的发展,来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只有真正的阅读,才可能真正谈得上理解和欣赏。 ”同时,他还提出,当下,全球化进程加快,任何一种文学都应该在国际文坛中与他者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 “所以,我想,这样一种国际参照,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是有必要的。汉学家们提出来的意见值得我们思考。 ”
史国强也认为,在不过高估计顾彬观点的同时,也要尊敬他、感谢他,他毕竟是热爱中国文学的,而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用丰富的材料和严谨的态度说话。所以我们既不能把他的话都当真,又不能充耳不闻。比如他说到的几个问题:当代作家的外语水平、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生存方式、真诚的写作等等,都是我们要深刻反省的。
汉学家最关注莫言、余华、贾平凹、王安忆。余华的《兄弟》在法国的影响很大
说起在海外最受关注的中国作家,谢天振认为莫言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莫言应该是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最关注的中国作家,还有余华、贾平凹、王安忆,这几个都是排在前面的。最近,《狼图腾》在国外很受欢迎,它恰好契合了当下人们十分关注环保、伦理等问题这样一个大环境。一部中国的文学作品被外国接受,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谈文学接受,一方面要看文学本身,另一方面也要看接受的环境。 ”
上世纪90年代初,谢天振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作报告,所谈的话题是西方科幻小说与中国武侠小说的比较。 “当时,我在报告里提到,中国的科幻小说其实是不发达的,但是,科幻小说在西方就很发达,甚至是大学里一门专门的课程。我认为,原因来自于民族特性。西方人跟中国人都是地球人,都有想象力,不过,一个更偏于幻想型的想象,一个更偏于务实型的想象。西方的科幻小说喜欢写外星,但是,在中国的想象力不在那方面。所以,电影《星球大战》在美国的票房很高,但是,在中国却反响平平。中国的想象力常常要通过务实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首先提供一个规定的情节,设定一个非常有真实感的时间和空间,但是,在这样一个务实的空间里所发生的故事却是充满了想象力的。而随着中国年轻一代的成长,他们的童年伴随着奥特曼、阿童木,于是,他们对科幻小说的接受程度会比上几代人好得多。 ”因而,谢天振认为,文学的接受是由许许多多的因素共同在起作用,“不同成长背景的人对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也是不同的。 ”
另外,许钧认为,现在中西文学交流远远多于过去。 “如果说我们中国的文学在国际文坛上被别人了解得还算少的话,那么,实际上,与20年前相比,这种陌生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的文学在逐渐被世界所关注。比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贾平凹的《废都》,还有莫言、苏童、毕飞宇、铁凝、池莉等等作家的作品,都在国外开始被当地读者和评论界所关注和接受。 ”许钧的研究领域是法国文学,因此,他对法国的情况更为了解,根据他的观察,通过一些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中法文化交流年,中国的一批优秀文学作品被介绍到了法国,并且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像余华的《兄弟》,反响非常热烈。因此,我觉得较之以往,是有根本性的变化的。 ”
余华的小说《兄弟》在法国的反响可以用轰动来形容。许钧表示,法国有很好的汉学传统,法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数量也比较多,大约有200多本书。 “无论是中国对外国文学的介绍,还是外国对中国文学的介绍,首先要有认识,所谓的认识就是要理解。葛浩文说过,他承担了很大的责任。他的责任在于要真正地把他认为美国人可以接受的中国的好作品介绍给美国人。如果说他介绍的是一位不好的作家或者是一部不好的作品,那实际上等于是扼杀了美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和认识。而法国有非常好的汉学传统,对中国的文学还是有识别的眼光的。”
海外销量最高的是卫慧的书。部分外国读者对中国有偏见,希望看到中国不好的东西,越丑陋越烂他们越想看
不过,陈众议同时指出,西方的大众眼光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仍然停留在一种不无偏见的猎奇心态上,还没有用一种平常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文学。 “当然,不是全部如此,但至少部分是这样的,或者说大部分外国读者还停留在这样的状态。他们对中国的大背景和现状还很陌生。而当下外国市场上的中国文学,不少是有问题的。 ”陈众议说,目前,国外翻译和引进的中国当代文学可大致分为三个类别,“一部分是好的,比如像莫言、阎连科、池莉、王蒙、苏童、余华这类严肃的作家;还有一部分是在国内受到批评和禁止的,外国读者对这部分文学的接受,特别能够体现他们的偏见,但是,这类文学恰恰在国外销量最好,比如卫慧等人的作品;还有一类是所谓的旅行文学、流散文学,它们大部分由在国内长大、其后旅居海外的作家所作。后者的创作心态非常复杂,其中不乏谄媚的因素,即拿中国的丑陋去取悦西方那些带有偏见的读者。在这三类文学之中,在海外影响最大、接受面最广的应该说还是第二类。卫慧的书销量最高。另外,贾平凹的《废都》销量也不错,其中就有曾经被禁的原因在里面。那些带着偏见的外国读者,希望看到中国不好的东西,越丑陋越烂他们越想看,这种需求与相对纯粹的文学欣赏相去甚远。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些不是最好的文学,但是他们就是想看,而且乐此不疲。 ”
谢天振认为:“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其实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当初,我们是怎样翻译、认识外国文学的呢?林纾是第一位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引进中国的翻译家,为了能让中国读者接受,他在翻译时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今天,我们的翻译事业可以说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而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其实是从最近这二三十年才开始的。所以,希望他们像我们理解他们那样来理解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了解他们,比他们了解我们要多得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但是,往往被忽略掉了。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就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文学有误解,甚至有指责。 ”
来源: 辽宁日报 记者:王研